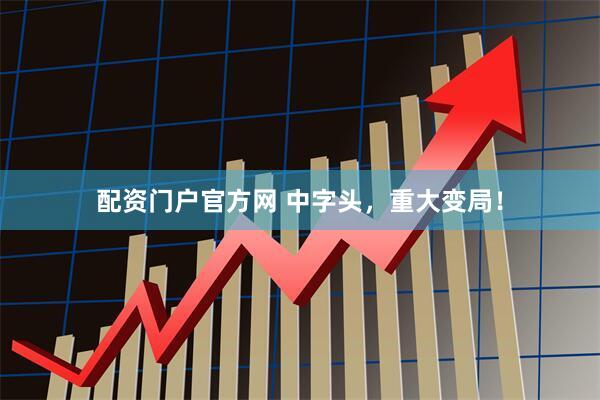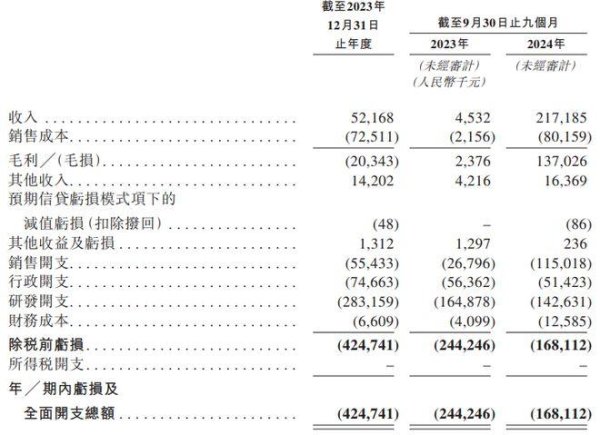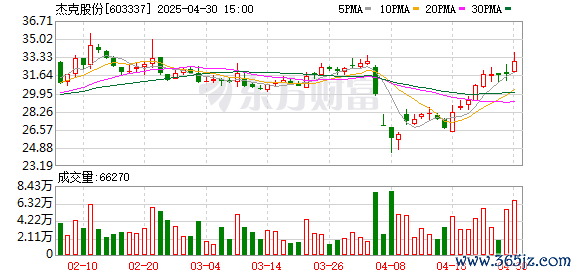股票10倍杠杆正规平台
股票10倍杠杆正规平台

哈萨克族是搬家最多的民族,他们又称之为“转场”。转场是一场通往夏天的缓慢旅程,赶着上千牛羊在风雨、泥泞与烈日之间行走。
今年夏季,我们随叶尔力克和他的妻子玛尔江,转场前往那仁夏牧场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快,唯有转场,还保留着缓慢的、坚定的美。
我问玛尔江,山里的日子孤独吗?她笑着摇了摇头。她喜欢山里,城市的日子太无聊,她总想回到大山。她边说着,手里边不紧不慢地收拾着早餐剩下的包尔萨克和酥油,晨风吹乱了她额前的碎发,转场要开始了。

我们到达时,叶尔力克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。他的马儿静静地站在一旁,鬃毛在风中摆动。阳光暖融融地洒在他身上,这个短暂的歇息,就是长途转场中最宝贵的慰藉。
看到我们来了,他热情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。牧民的热情总是直白而不造作,干净爽利。我们将一起从深山的春牧场出发,沿着边境线,一路转场至那仁夏牧场,为期两天,跨越80公里。

羊走得慢,早上五点就要收拾好所有东西出发。新疆的五点,相当于内地的三点。那晚我没怎么睡,脑子里装着的全是清晨山路中羊蹄踏过的声响。
天还没亮,空气清冽得像是刚刚洗过,露珠裹在每一根草叶上。600多只羊在晨雾的沉默与寂静里缓缓踏上旅途,整个草原还没完全醒来。这种宁静,不是城市早八的闹钟能打破的,它是清晨连鸟都不忍惊扰的沉默,被羊群呼出的热气慢慢温热。

刚出发,我和我的马“霸王龙”都兴奋得很,一路小跑,跑前跑后。
老羊们认得路,带领羊群熟门熟路地踏上早已被无数羊蹄、牛蹄踩实的牧道,三只、五只、七只.....乌泱泱、呼啦啦、吵哄哄,像洪水一样从山坡上倾泻而下。山羊、绵羊、白的、褐的、大的、小的,拥挤着、追赶着、喊叫着。偶尔几只小羊跑偏去吃草,我们还要去把它们哄回来。
阿勒泰大尾羊的屁股,在颠簸中晃得欢腾,它们摇着屁股走在前头,像是在跳舞。生活的路从来不是直线,而是一场踉踉跄跄的圆舞曲。

现在正值阿勒泰的转场季,山谷间到处是正在搬家的牧人,赶着牛、羊甚至骆驼。随着时代变化,转场不再全靠畜力运输,但牛羊群依旧由牧民骑马赶着,毡房衣被等家当则靠车运。
我们走的,是一条勉强能开车的土路,车跌跌撞撞地跟在羊群后面。每隔几十米就是一支小队,汽车在动物之间缓慢穿行,以每小时五公里的节奏慢悠悠地挪着。

在千年的古牧道上,数不清的马牛羊绵延数百公里,道路曲曲折折,队伍弯弯曲曲,有多长的队伍,就有多长的尘土。地面腾起三四米高的黄色尘土,把羊群淹没其中,在日出的照射下是热气腾腾的橙红色,弥散在山野之中。

路过一条清浅的小河,水清澈见底,鹅卵石在水下闪着湿润的光。大部队沿着河边前行,而叶尔力克的羊群却斜着爬上了溪边的山坡。“他们认得这条路,年年都走。”他说,“不是最近的,也不是最好走的路,但羊认识了习惯了,再难也得走。”
那条路果然难走。溪流两边都是错综盘旋的松树,树杈横伸出来,要时时留神别被抽了脸。一边盯着羊,一边还得控马穿过石头与树根间的缝隙。马身一侧擦着树干,树皮蹭出一道浅痕。骑在马上,整个人像被山林逼进一条缝隙中,动弹不得。

终于穿过林子,眼前豁然开朗。一侧是并不太缓的下坡,另一侧是更为陡峭的上坡,布满石头。我本以为要下山,羊群却一个转弯,径直爬上了陡峭的山坡。
肉眼看,那是一条近乎垂直的碎石山坡。马蹄穿着蹄铁,踩在石头上本就打滑,更何况如此刁钻的角度,我的心跳得不成节奏。

马走两步便得歇一口气,呼吸粗重,鼻孔里喷出一股一股白雾似的热气。蹄子踩在碎石与泥土混合的山道上,不时打滑,前蹄抬起落下都变得迟钝而沉重,每前进一步都像是拖着一整座山在爬。羊群在前头缓慢地移动,边走边低头啃草,仿佛没有察觉这天险似的陡坡。
越往上,坡越陡,路也越窄,回头便是陡坎下坠的山谷,一眼望不到底,风从谷底涌上来,带着凛冽的凉意,仿佛在耳边警告。我拍拍霸王龙早已被汗水浸湿的脖颈,紧紧抓住马鞍前的桩头。

站在山脊上望去,远方的平原上聚集着几十群牛羊,如一幅幅缓慢流动的画。叶尔力克说:“他们在排队等边防开门。这里是边境,管理严格,每天十点左右会开闸放行牧民。”我这才意识到——走了一路,现在居然还不到十点。
时间在山里,是被风揉碎的,不那么规整地流淌着。

到了下午一两点,我们已经骑行了八个小时。我没看表,但肚子比表准得多,按时叫了起来。可眼前除了漫无边际的牛羊群,只有飞扬的尘土。
马跟着羊群摇摇晃晃地走,慢得像蜗牛。马儿有些着急,步子比羊快,时不时就超了过去。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勒停它,等着羊群悠悠地往前挪。
人坐在马背上,也跟着马的步调,一会前一会停,被颠得晕晕乎乎。原本还有点兴奋,可这点劲头在重复中被悄悄磨光了,像水壶煮干了一样,悄无声息地冷了下去。

次日的行程更难,进入那仁草原的山道起伏极大,要翻越多座山岭。
林间穿行几个小时,视线在树影里斑驳。穿过最后一片密林,一整片宽广的草原在眼前敞开胸怀。河水从中间蜿蜒而过,像是谁用银线绣出的褶皱。远处雪山沉静,牛马像散落的云影般踱步其中,偶尔能听见悠远的吆喝。
“那仁牧场”的牌子赫然出现在眼前。“上面是天,深蓝明净;下面是草场,一碧万顷;森林在右边浩荡,群山在左边嶙峋;身边的河流淙淙,奔淌不息;前面是山谷的尽头,后面是山谷的另一个尽头……”此刻,我忽然理解了李娟笔下的世界。

那仁牧场位于哈巴河县北部高山区,这里阳光充裕,水草丰美,以“天堂牧场”著称。每年五六月份开始,各种山花竞相绽放,牧民的毡房星罗棋布,牛马羊群散落草原。登高望远,杨树松柏和白桦林相间,绵延数里,湛蓝的双湖清澈透亮,尽收眼底。
但这里,还不是终点。
拐进山谷时,叶尔力克抬手指了指前方的大山,说:“翻过那~~座山,就到了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望去,山高得不讲理。我悻悻地点点头,觉得“那~~座山”好像确实不远了。拍了拍霸王龙的脖子,收拾好四散在草地上懒洋洋吃草的羊群,继续前进。

风景再美,也挡不住突如其来的暴雨。
新疆昼夜温差大,山区气候多变,十里不同天,说风就是雨。如遇雨雪、大风、雷电、冰雹等极端天气,那更是雪上加霜。转场途中,哪怕大太阳天,牧民都会穿着或带着厚厚的外套。
天是一瞬间黑下来的,雷声在四面八方炸响,冰雹夹着大雨倾泻而下,马匹一瞬间便湿透了身,身上的衣服也像直接泡进了冷水里。我们赶紧下马,手忙脚乱地扯出马鞍后捆着的雨衣往身上套。

上了坡顶,眼前只有连绵的群山和倾泻而下的大雨点子,看不到丝毫毡房和木屋的痕迹。回头问叶尔力克,他笑着说:“还要再翻过眼前的那~座山。”这回“那”字说得短了很多。网上段子说新疆人对远近的衡量,就是靠那个“那”字的长短来判断的——“那~~座山”,就是遥不可及;“那座山”,才是真的快到了。
雨越下越密,仿佛整个山谷都沉在水底。我们淋着雨,一路哆嗦着继续往前走,沿着被马蹄踩得松软的牧道钻进了第二个山谷。我抬手挡了挡雨,眯着眼往上望,那山比第一天爬的石头山还要高,也更陡。虽不是赤裸的石头山,但一整片草甸已被雨水浸透成了泥沼,马一脚踩下去发出“咕唧”一声,像踩进了糯米团。

雨里赶羊难得多,马在坡上打滑,羊群也不再规规矩矩沿着牧道走,而是走“Z”字形上山。这一来,它们就不再一前一后地排着队走了,而是见缝插针,边走边吃,慢悠悠地自己找路。
才一眨眼,六百只羊就像六百滴水珠落在山坡上,呼啦一下子,全散了。你追上一个,那边两个又跑远了;这边刚拢好一片,那边又吃嗨了开始折返。
山坡上、山坡下,放眼望去全是羊,散开的羊。

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,原来前几天沿着山谷走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。羊群乖乖地、规规矩矩地走在牧道上,像被放在传送带上。但雨中的山坡就不一样了,羊会自己挑路走,完全不讲规矩。你喊破喉咙,它也不过抬头看你一眼,又继续埋头吃草。
羊不着急,它们见过太多风雨了。急的是我们,被困在坡上左突右冲,走到最后,嗓子哑了,马喘粗气,人也开始恍惚了。

奋斗了一个多小时,眼前的坡快爬完了,雨点也终于变小。如果不需赶羊,骑马上坡也不过两三分钟。
这时,一个牧民骑着摩托车从山腰“突突突”地驶来,全身裹着塑料雨衣。叶尔力克说,那是他邻居,这片山谷的牧民们总是这样,互相搭把手。小电驴替下了累瘫的马。到达山顶,放眼望去又是一片群山,但这次我们能看到邻居的白色毡房了。叶尔力克说:“不远了,那边就是了。”
没有拖长音,听得出来真的不远了。

不多时,叶尔力克的木屋出现在接近山顶的平坡处,云层低得像是伸手就能摸到。对面的山谷就属于哈萨克斯坦了。马刚卸下鞍,天边便升起一抹完整的彩虹,叶尔力克的媳妇玛尔江说:“出了彩虹,今天就不会再下雨了。”
玛尔江早就跟着车来到了木屋,正在煮奶茶,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味。用不锈钢小勺挖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酥油,伸进热腾腾的碗里。酥油瞬间融化并扩散,在奶茶的表面形成一层金黄色的漂浮物。奶茶唤醒了似乎还没睡醒的大脑,感觉浑身有力。
放羊的生活,并不总是如诗。伴随的更多是灰尘、烈日与重复,是一个人在辽阔中与无尽时间的较量。但正是这种“不像诗”的日子,被他们过出了比诗还真挚的底色。在这片辽阔之中,每一次重复都藏着生活的智慧与喜悦。

晚上我们在叶尔力克木屋旁的小山坡上扎下帐篷。大家围在帐篷里,说话、喝酒、吃馕,彼此谁都不急着睡,聊起各自的趣事,也聊刚才的羊群怎么在暴雨里消失不见,又怎么慢吞吞地走回了我们的身边。
毡房里是烟火气,毡房外面是山、是风、是星、是整整齐齐被赶进圈里的羊。忽然有人大声笑,笑声一下子飞上了天,又被风温柔地吹远了。远处是牛羊马的咀嚼声,和时不时的响鼻声,一切都让人觉得心安。
编辑/Lili、Tasia
文&图/李晏萍
设计/April

仁信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